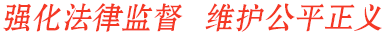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理念进步与制度完善
一、新发展理念得到具体体现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即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在民法典总则编中首先体现为“绿色原则”,即第九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中得到进一步具体体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从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至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共7个条文,相比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的4个条文,不仅仅是条文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不再仅局限于环境污染责任,还增加了生态破坏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一般条款。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该条专门针对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责任以及修复费用承担进行了规定。与此衔接,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对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侵权人应赔偿损失和承担费用的具体范围进行了规定。
回溯立法史,对于污染环境应承担侵权责任这一内容,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已有规定,体现了立法者的远见卓识。这一内容在侵权责任法中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但并未跳出因污染而承担侵权责任的范围。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污染层面,不仅污染会造成环境破坏,生态破坏也是一种破坏,应当对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作出一体化规定,从而抑制这类侵权行为。例如,对于外来物种带来的影响,实践中已有较强的认识。某县农业农村局水产工作站在工作检查时发现当地一库区养殖的鱼类中含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鲈鱼,掠食性强,属外来物种,可能对本土鱼类造成影响,立刻报告县政府,县政府即刻召开研讨会并邀请检察机关参加。检察机关参会人员就外来物种入侵可能破坏当地水域生态链和生物多样性发表了意见,提供了检察建议。最终违法网箱养鱼设施全部拆除,养殖的鲈鱼也已依法处置,外来物种入侵威胁得以消除。①这一案例说明,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实务工作中已经有了较强的对于生态保护的认识。这也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权利救济与行为自由更加平衡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更为注重权利救济与行为自由的平衡。侵权责任法虽然以救济权利为己任,但在救济权利时不能妨碍行为自由。这一点在侵权责任编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一)修改被侵权人过错的适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相较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少了一个“也”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是立法理念和立法内容的重要变化。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也”字,说明只有在侵权人有过错的时候,被侵权人的过错方可成为减责事由。也就是说,这一减责事由的适用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前提。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去掉了“也”字,意味着该条减责规定,不仅在侵权人有过错的时候可以适用,在侵权人无过错的时候也可以适用。即不仅仅适用于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也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扩大了该减责情形的适用范围,进一步兼顾了行为自由。
(二)增加自甘风险的规定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一条在学理上被称作自甘风险规则,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新增内容,在侵权责任法中并无规定。该条规定意味着在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中,除非其他参加者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对自愿参加者受到的损害,加害人不必承担责任。这一规定进一步减轻了参与者对参与文体活动的担忧,参与者可以不必因担心承担责任而小心翼翼,甚至望而却步。实践中,有些案件的处理往往需要参与者承担责任或进行补偿。例如,在“杨玉荣诉宾成健康权纠纷案”②中,原告杨玉荣和被告宾成同为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篮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170联盟的成员。在2013年5月14日举行的比赛中,原告杨玉荣作为进攻方跳起准备投篮,被告宾成作为防守方,对原告的投篮进行封盖,致使原告杨玉荣落地时右手受伤,但该场比赛的裁判认定被告宾成的防守行为并未犯规。事发后,原告杨玉荣的伤势经司法鉴定认为,“被鉴定人所受损伤目前的伤残等级可相当于《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七级伤残”。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请求被告赔偿1046530元。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被告没有过错,不承担过错侵权责任,但均判决被告应予以补偿。一审判决被告补偿原告40万元,二审改判为补偿10万元。类似案件在实践中并不少见,尽管是补偿,但也给文体活动的参与者带来了不小的顾虑。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自甘风险规则,则可减少或打消这种顾虑,从而获得更进一步的行为自由。
(三)规范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与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相比较,以“依照法律的规定”代替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这一变化使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更为规范,限制了法官在这一原则适用时的自由裁量权。
在司法实践中,在原被告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法官往往会援引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判决补偿。如前述“杨玉荣诉宾成健康权纠纷案”即为此种情况。但这一条的过度适用给行为人的自由带来了较大的妨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公平”的本意。例如,在“田九菊诉杨帆生命权纠纷案”③中,因段小立在电梯内吸烟,杨帆予以劝阻,二人发生言语争执。段小立与杨帆走出电梯后,双方仍有言语争执。后段小立因心脏病发作猝死。田九菊(段小立之妻)诉至法院要求杨帆对段小立之死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杨帆劝阻段小立吸烟行为未超出必要限度,也无肢体冲突,还在段小立身体出现状况时积极予以救治。但一审法院仍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判决杨帆补偿田九菊1.5万元。该判决作出后引起较大争议。二审法院认定杨帆劝阻段小立吸烟行为属于正当劝阻行为,且自始至终平和理性,对段小立的死亡没有过错,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审认为一审判决适用公平原则判决杨帆补偿田九菊1.5万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改判理由中,二审法院特别强调,杨帆对段小立在电梯内吸烟予以劝阻,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一审判决判令杨帆分担损失,让正当行使劝阻吸烟权利的公民承担补偿责任,将会挫伤公民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既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也与民法的立法宗旨相悖,不利于促进社会文明,不利于引导公众共同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④这一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过度适用或不当适用现象,使得司法判决进一步体现了“公平”本意。但该二审判决只是少数个案,更多的案件存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情形。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与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的规定密切相关,法官在适用过程中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该条得以广泛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进行了修正,把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时的损失分担,限定在有法律规定的场合,将会使“公平原则”的过度适用受到限制,使之体现真正的“公平”,在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到行为人的自由。
三、对受害人的权益保护更加充分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注重权利救济与行为自由平衡的同时,对受害人的保护更为充分。
(全文详见《人民检察》2020年第11期或请关注《人民检察》微信公众号)
 大荔检察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大荔检察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大荔检察头条号二维码
大荔检察头条号二维码 大荔检察新浪微博二维码
大荔检察新浪微博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