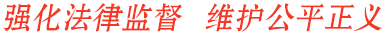马小红:天理国法人情兼顾法律理念的当代传承
摘要
尽天理、顺人情是中国古代立法、司法的原则。天理,是中国古代法律最高的价值追求,也是裁断是非善恶的最终依据。而人情则是天理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是法律维护而不是对立或遏制的对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只有体现了天理人情的法才称得上善法。对天理的皈依与对人情的兼顾,使中国古代法律在设立与实施中不仅以惩恶为目的,更以扬善为使命。天理国法人情兼顾法律理念在现实中的传承,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而且有助于形成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中国古代法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刑”的负效应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即“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刑罚是惩罚犯罪、彰显正义、维护社会安定祥和的利器,但运用不当,也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工具。中国古代法律对天理国法人情的综合考量,大大减弱了刑罚的负效应。因为国法对天理的皈依与对人情的兼顾,使“法不仁不可以为法”的善法观念深入人心,刑罚惩恶扬善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刑法有限性的缺陷得以弥补。
一、天理
天理一词是从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后开始流行于朝野的,理学的中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自宋以后几乎家喻户晓,而明清的州县衙门中也必有天理国法人情的匾额高悬于门楣。但天理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则是源远流长,而且十分普及。先秦时期,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法家等都对天理进行过阐述。“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直接源于儒家经典《礼记》中的这段话:“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由此看出,《礼记》对天理、人欲、世道之间的关系持有这样的论断:天理存,则世道治,民可安居乐业;惑于物质享乐而无所节制的人欲兴,则天理灭,世道乱。天理就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必然),即人们所必需(应当)崇奉、遵循、服从的规律、法则、秩序。天理是统摄万事万物最高的客观存在,是人人应当遵循的最高准则。这个最高准则在朱熹的阐述中则是“当然之理,无有不善者”的天赋人性,故“性即理也”。
天理赋予人们应有的善性,是儒家纲常名教中一贯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与忠、孝、节、义。在中国古代伦理法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与忠孝节义不仅是人类社会应有的道德共识,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体现。国家的法律必以此为皈依方能助成教化,成为善法,否则法律便失去其所应当具有的“善”性,失去其应有的惩恶扬善的作用。从以下史实与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法律对天理的皈依。
《史记》记载,商汤出巡,见有人张网四面捕捉鸟雀,并祷告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商汤见后,感叹四面张网对鸟雀过于残忍,不合人之性善的天理。于是将四面之网去掉三面,并重新祷告,愿飞翔的鸟雀能躲过网捕,只有不用命(不听从劝告)者落入网中。天下的诸侯听到这件事,感叹商汤的仁义之心惠及禽兽而归顺了商汤。明代著名宰相张居正将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编入《历代帝鉴图说》中,教导皇帝对待百姓应怀有仁义之心。“网开三面”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形容及赞扬谨慎用刑、刑罚宽大的成语。
作于西周穆王时期的《吕刑》,将形式上相同的“五刑”区分为“祥刑”与“虐刑”。以刑罚为工具,对百姓大开杀戒、残害善良无辜、导致天下大乱的蚩尤所作的“五刑”为虐刑;而除暴安良、惩恶扬善、致民安居乐业的尧舜所用的“五刑”则为祥刑。虐刑与祥刑虽然同是五种刑罚,但适用的社会效果却截然不同。其分水岭就在于用刑者是否以善心对待天下百姓;用刑的目的是保护善良,还是残害善良;效果是天下大治,还是天下大乱。
汉代的《春秋》决狱也是将天理作为最高价值而追求的。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辑录了一则董仲舒《春秋》决狱的事例。言君主狩猎,得一幼麂,让大夫带回宫。在回宫的路上,大夫见幼麂之母追随哀嚎,心有不忍,便放归了幼麂。君主很生气,要定大夫之罪。在议定大夫罪名的过程中,君主得了重病,恐怕自己性命难保,诏大臣以托孤。这时,君主想起了放归幼麂的大夫,心中感叹:大夫实在是一位仁义之人!对一只麂子尚能施恩相救,何况对人!于是释放了大夫,并委任大夫为太子的师傅。有人问董仲舒,君主这样做,对吗?董仲舒答道,(礼有规定)君子不得猎捕幼兽。当君主猎捕幼麂时,大夫未能及时以礼劝谏阻止,这是“不义”的行为。而在带幼麂回宫的途中,大夫感念麂子的母子之情,心生恻隐而放归幼麂,虽然是废君命,但判徙刑就可以了。判大夫徙刑,是因为大夫在君主捕获幼麂时没有以礼劝谏君主,并不是因为大夫废君命。可见,在董仲舒的价值观中,体现天理的仁慈之心、礼义之行远比君命重要。这就是荀子在《臣道》中所倡导的从道不从君。
由于法律的最终皈依是天理,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才格外注重立善法以治国安民,并力求在司法中体现天理。一旦法律与天理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冲突,天理往往会成为裁断者的最终选择。因为天理才是人类社会所应具有的永恒价值观。
二、国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赞叹《钦定大清律例》时言:“或略迹而原心,或推见以至隐,折以片言,悉斟酌于天理人情之至信。”由此可见,立法时充分体现天理人情,使国法与天理人情相一致,是中国古代立法、司法的宝贵经验。从天理、国法、人情多角度考量法律的社会效果,才符合中国古人对善法的追求,对正义的解读。基于对天理人情的“斟酌”,中国古代的法律充满了对天理的崇敬与对人情的体察。本文仅以下列中国古代常设之法说明之。
(一)赦制
赦是对罪犯减免刑罚的一种制度,也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周礼∙秋官》中就有司刺掌“三赦”的记载。三赦,即对老幼、过失、精神不健全的罪犯予以赦免。还有一种赦制,是属于帝王的专门权力,即在普天同庆的日子,如改朝换代、皇帝登基、册封皇后及太子、天降祥瑞以及遇有天气激变之时,帝王都可以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除“常原不赦”的犯罪之外,均可以减免刑罚。如,唐太宗即位时发布赦令:“自武德九年八月九日昧爽已前,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系囚见徒,悉从原免。武德元年以来,流配者,亦并放还。”类似的赦书在汉代以后不绝于史。古代大赦制度的设立,为的是展示帝王为天下父母的仁慈情怀。《汉书∙刑法志》引古语说明帝王应有的这种情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即帝王犹如家长,百姓是如孩童一样的子民,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如果有一人向隅而泣、不得其平,帝王则应为之凄怆于心。
古代的赦制历来有很多争论。主张实行赦制的人,以儒家的思想为理论,认为赦制表现了帝王爱民如子的仁者之心。反对实行赦制的人亦以儒家的思想为依据,认为大赦减弱了刑罚保护善良的威力,是妇人之仁。因为大赦常常会使罪犯逃脱惩罚,助长犯罪者的气焰。南宋文学家、思想家洪迈的《容斋随笔》中记,婺州有一富豪,为人刻薄,下乡收租时被一佃户父子四人所杀。衙门审理结案之时,恰逢皇帝发布大赦令,父子四人获赦出狱。出狱后的杀人犯,竟然跑到了被害人的家中进行挑衅,问被害人的家属何不下庄收谷。为了体现天下父母的仁义之心,皇帝的赦令还会干涉到民间的经济生活。南宋孝宗发布的大赦令中竟有赦免天下债务一项:“凡民间所欠债务,不论久近多少,一切除放。”赦令一下,放债的富豪之家因血本无归而群起反对。于是皇帝又下赦令,改为只偿本钱,免除利息。
虽然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赦制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赦令如果过于频繁会使为恶者猖獗,善良的百姓手足无措。但是,因为赦制是以法律的形式直接体现了帝王对天下百姓的怜悯体恤之情,所以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自汉代以后一直存在。
(二)录囚(虑囚)
录囚是皇帝与官吏按制对记录囚犯的罪状进行讯查的制度,其始于汉代,是儒家慎刑思想的制度安排。录囚的目的在于发现、纠正、平反错案,减免对情有可原犯罪者的刑事处罚。史载东汉光武帝是一位留心庶狱的皇帝,常临朝听讼,躬决疑事。他的后任明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常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唐太宗纵囚”是中国古代皇帝录囚中的一件著名事件。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亲录囚徒,见死刑犯中情有可悯者390人,纵之还家。唐太宗与这些死刑犯约定,希望他们第二年的秋天自觉按时返回朝堂就刑。结果,这些死刑犯在第二年的秋天皆如期而至,没有一人迟到。为表彰他们的诚信,太宗免除了他们的死罪。时隔数百年后的宋人欧阳修作《纵囚论》,对唐太宗的纵囚提出质疑,认为唐太宗的纵囚之举有违人情,不足为常法,更不应为后世效法。将《纵囚论》收入《古文观止》的吴调侯、吴楚材赞同欧阳修的观点,认为太宗纵囚,囚自来归,俱为反常之事。可以看出的是,欧阳修也好,吴调侯、吴楚材也好,反对的都不是录囚制度,而是唐太宗在录囚中的非常之举——纵囚,反对的原因则是此举有违人之常情。
除帝王亲自录囚外,派专门官员及地方上级主管对下级的司法裁判按时进行复核也是录囚的重要内容。汉昭帝时,隽不疑为京兆尹,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宋代,宋太祖每亲录囚徒,专事钦恤。凡御史、大理官属,尤严选择。开宝二年五月,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钮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作为一项常行的制度,录囚对杜绝司法实践中的草菅人命、严刑峻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三)存留养亲
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制的农业社会。人的一生,生老病死大多由家族负担,养子防老成为人之常情。存留养亲便是这样一项充分考虑到社会实情的法律制度。唐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中又无期亲成丁者,犯死罪(非十恶)应该上请处置;犯流罪者,权留养亲。权留养亲制度为后世立法所继承,在《大清律例》中称为存留养亲,规定于《名例律》中。清律规定,凡死刑犯,家中有年七十以上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等尊亲长,或父母等尊亲长有重病需要侍候看护,家中又无十六岁以上的成丁男子,应将罪犯所犯的罪行写明白,上奏,由皇帝亲自裁决,多能获得减刑。如果是流刑犯或徒刑犯,则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在此后颁行的“例”中,又对律文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如,如果是杀人罪,被害人若是家中的独子,家中亲老亦无人侍奉,则杀人之犯不准留养。这种补充完善显然也是进一步斟酌了人情的结果。
存留养亲不仅符合儒家提倡的孝道,而且也符合儒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治国理民主张。
(四)容隐制度
对天理、人情的关注,使中国古代法律对正义有多维度的观察和阐述,自秦以后,法条主义在中国古代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论语∙子路》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朱熹注释道:“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此处的“直”,可以理解为公正、正直。在孔子、朱熹等儒家学者看来,当法律与天理、人情发生冲突时,正义的裁决当然应当倒向天理人情,而不是机械的法条。因为天理人情是自然赋予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观。子证父违法,违背了天理人情,即使合乎法律也不能称之为“直”。
自汉代对秦严刑峻罚反思批判以来,法律上的容隐制度便逐渐形成。汉宣帝下诏,子孙首匿犯罪的父母、祖父母,妻子首匿犯罪的丈夫,都是法律所允许的。反之,尊亲长首匿犯罪的卑幼,除死罪需要上请减免外,其他罪也不负刑事责任。汉以后,历代律典都有容隐的规定。如,《宋刑统∙名例律》“有罪相容隐”部分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五)死刑复奏制度
上天有好生之德,人命关天是中国古人的信条。基于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格外强调慎用死刑,“改重从轻”“化死为生”是大赦、录囚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曹魏时将死刑的处决权收归到皇帝手中。魏明帝经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遇有重大案件,他常到听讼观亲自审判。青龙四年(公元236年)魏明帝下诏对郡国一年之中判处死刑“尚过数百”深表忧虑。他指出,有些死刑犯,有司认为应当缓刑,正在上报乞恩,皇帝尚未下旨,死刑已经执行。魏明帝指责这种行为非所以究理尽情也,故下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者应当将有关案情文书奏报皇帝,朕将思所以全之(保全死刑犯的性命)。这便是死刑复奏制度的开始,其目的在于使法律能够究理尽情,尽量避免适用死刑。
死刑复奏制度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代形成死刑三复奏。三复奏,就在死刑执行前奏报皇帝三次,使皇帝有时间了解案情,根据天理国法人情多方面的考量,谨慎地作出杀或不杀的决定。唐太宗则将京师地区的三复奏改为五复奏,拉长了死刑执行前的奏报时间和次数,以便皇帝有更充分的时间进行斟酌。
以上的国法告诉我们,天理人情才是国法的最终价值追求,究理尽情的国法才是人们心目中的善法。
三、人情
天理国法人情中的人情,在中国古代人们心目中有特定的含义,这是上天所赋予人们美好的自然秉性。流传广泛的《三字经》中概括:“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即人人都具有《礼记∙礼运》中所言的人所应当具有的“人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友)、弟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也是家族、社会、官场中人与人交往的“大法”。孟子言,圣人忧虑人们在吃饱穿暖之后,丧失人之道,而与禽兽无别,所以设官教以人伦,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以说,人情是天理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朱熹认为,即使圣君尧舜统治天下,也不过是率性而已,而所谓率性即循天理是也。
帝王率性的统治,就是以仁驭天下。当法律与人情抵牾时,君主应当展示仁者的心怀。汉人刘向在《说苑》中记,大禹巡视地方,见到被押解的罪人时而怜悯流泪,同行的人认为这些罪人是因为犯了罪而被惩罚的,罪有应得,君王不必为他们痛心。禹却说,尧舜时期的人与尧舜同心同德,而我为君主,百姓却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见到犯罪的人,反躬自责自己为君不如尧舜、使民陷于缧绁之中,表现了禹对天下百姓的仁慈之心,这一故事也被张居正作为帝王楷模收入了《历代帝王图鉴》之中。《荀子∙宥坐》中记载的孔子断父子相讼的故事,也生动阐释了善法的人文精神。孔子为鲁国司寇时,对至官府争讼的父子二人拘而不审。三个月后,其父悔讼,请求撤诉止讼。于是,孔子释放了这对父子。季孙氏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埋怨孔子欺骗了他。因为季孙氏认为,孔子曾对他说过应该以孝治理国家。如今有父子相讼的案件,杀了与父相讼的儿子,不是正好可以惩罚不孝吗?但孔子却将他们父子一起释放了。孔子的学生冉子将季孙氏的不满告诉了孔子。孔子感叹道:“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即统治者对民众不实行教化而粗暴地用刑,等同于杀戮无辜之人。孔子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教化,是因为确信人之善性通过教化是可以保持或恢复的。对争讼的父子拘而不审的三个月中,孔子等待相讼的父子能人性发现,为自己的言行而感到羞耻。事实果然如孔子所期望的那样,其父撤诉“请止”。
大禹下车泣罪与孔子断父子相讼的故事,都是中国古代的经典案例,为后世所效法。《汉书∙刑法志》引孔子之言以明辨善法与恶法在实施过程中的不同:“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执法者不失有罪,末也。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在中国古代,只有兼顾了天理国法人情的法律才称得上是善法,“没有天理的国法乃恶政下的乱法,没有人情的国法乃霸道下的酷法,都不算是助长人类社会生活向上而有益于国家社会的法律”。
四、优秀法律文化的当代传承
在天理国法人情兼顾的法律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律在设立与实施中有着对社会发展全方位的考量。其不但要求有法必依,而且要求法律是符合天理人情的善法;不但要求违法必究,而且要求法律在惩罚犯罪、保护善良的同时也能促使违法者洗心革面,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这些优秀的法律文化理念在现实的立法司法中被自觉地传承下来。如,检察机关在依法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同时,坚定地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用足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大限度减少、转化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将司法救助融于社会救助格局中,检察机关主动加强与民政、教育、卫生健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沟通,2021年1月至11月实际开展司法救助2.7万件,切实加强了对生活困难当事人的司法救助力度,使其同样能够感受到法律的正义和温度。
天理国法人情兼顾的法律理念在现实中的传承,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而且有助于树立起人们的法治信心与信念,以消除戾气,形成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微博公众号
微博公众号 两微一端
两微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