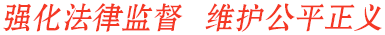最美的书房
陕西省图书馆曾经举办过一次“寻找最美书房“的活动,参赛作品中,那一个个或温馨浪漫、或简洁大方、或古朴厚重的书房,连我也心驰神往。
除了专门的书房,可以读书的地方还有很多,古人就有“三上”之说,即马上、枕上和厕上。宋代诗人钱惟演曾说: “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现在的交通工具从马变成了汽车、火车和飞机,少了许多颠簸,在上面阅读也变得很方便。特别是在长途火车上,阅读不仅可以充实路途中的空闲时间,在窗外流动风景的映衬下,也更容易让人静下心来思考。枕上一直是读书的绝佳地点,古今皆同。至于厕上,有人说这时看书不利于身体健康,可是却有那么多人在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与其这样倒不如看几页书来得充实。
而我自己,却从来没有拥有过一间书房。小时候,父母辛勤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我的童年没有五颜六色的故事书,唯一搜罗出来的是一本不知年代的《大千世界》杂志和一本没前没后讲春秋战国成语故事的书,那两本书在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后变得愈发破烂。所以可想而知,当我从小学同学那里借来一本彩色封面的《365个故事》的时候,是怎样地如获至宝。
然而同学只答应借我一天,白天上完课做完作业后,我急切地将一行行的文字收入眼底,厚厚的一本书,我像春蚕啃桑叶一般努力,到了该睡觉的时候还剩下一大半,想着明天一上学就要将书还给同学,我是有多舍不得。严厉的母亲亲自监督我睡下,我却无法合眼。无奈,我摸索着爬起来,悄悄找到手电筒拿着书缩回被窝,继续看下去。虽然最终我还是带着遗憾将没看完的故事书还给了同学,可躲在被窝里看《雪孩子》并流泪的场景却成了自己童年最鲜明的记忆之一。
初中的炎夏,满地的西瓜秧叶子都快被晒卷了。肩负着看守瓜地重任的我坐在闷热的瓜棚里,贪婪地读着父亲从工地单位的图书馆借来的书,《牛虻》、《青年近卫军》、《最后一个匈奴》、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北欧神话故事选》……我的时限只有一个暑假,幸运的是,暑假结束的时候,父亲带回的近一蛇皮袋的书我基本看完了,没再留下小学那样的遗憾。
高中时代的我们,最喜欢在周末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门前那棵白杨树下,手捧唐诗或者宋词,大声吟咏,有阳光、有风的日子最好,阳光会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跳舞。发现特别喜欢的诗词的时候,就读给别人听,开心地和她们一起吟诵。
现在的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光便是睡前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挑一本喜欢的书,打开台灯,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一个梦境般的场景,我将书摊在最亮的地方,让它做了这个小场景的主角。这时,不管外面是秋虫低吟,或是白雪簌簌,甚或是狂风暴雨,都与我无关。我就像站在一颗只有我和书的星球上,孤独,却满足。
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副震撼人心的照片,一座被炸毁的图书馆,地上满是钢筋、水泥、瓦砾、被炸坏的书架和碎纸片,但就在这里,三位戴礼帽的绅士在挑选书籍和静静地阅读。
在这座图书馆里,没有了宽大的橡木桌,没有摆放整齐的书籍,有的是随时会重新开始的轰炸和随时丢掉性命的可能,但即便这样,他们仍旧选择了阅读,在废墟上。
阅读是不拘地点的,如果真要寻找最美的书房,那么,一颗热爱阅读的心,应该是那最美的书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