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员额制检察官退出机制的思考
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检察院 李劲峰 王文钊
【摘 要】 员额检察官遴选稳步推进,而退出机制建立明显滞后,极大地影响了检察机关各类人员的优化组合和动态调整。员额检察官的退出应分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两种情形,在程序的设置上应与遴选决定权相对应,在内部操作层面给予绩效考核委员会的决定权,最终决定权交由省惩戒委员会更为适宜。
【关键词】规律;主动退出;被动退出;对应:绩效考核
员额制检察官改革是检察机关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同志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检察官是检察机关人员分类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承担检察职能的最重要的角色。目前,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员额制检察官的遴选,为保证司法责任制改革了提供了坚实的人力支撑,面临“入额”的层层推进,“退额”必须及时规范,建立员额检察官推出机制形势所迫。
一、员额检察官遴选退出现状
(一)遴选状况。按照现行的《检察官法》规定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助理检察员均为检察官,其中助理检察员由本院检察长任命,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检察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并由上级检察院检察长提交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可见在实行员额制检察官改革之前,助理检察员的任命最为简单直接。但在国家实行统一司法考试的规定之下,成为一名助理检察员也是历经“大考”,经受考核检验,也实属不易。正由于助理检察员任命的方便,通常原来一个检察院检察官的比例可达政法专项编制的50%,有的达60%甚至更多。而大刀阔斧的员额制检察官改革,使原有检察官的格局被打破。员额制检察官是指检察院在政法专项编制内根据办案数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的检察官的人员限额。这是在原有的检察官群体中的再次选拔,触及的利益层面深入人心。按照中央规定,员额制检察官比例保持编制数内39%,基层检察院最高可扩大至40%。由于员额检察官比例的限制,从而使一部分原来的检察官必须转换身份,成为检察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如今通过遴选制度选拔员额检察官步入正轨,从三批试点检察院一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是通过“考核”或“考试+考核”的方式,由本院按照一定比例推荐员额检察官人选,逐级向上级院报告,最终由高检院、省级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确定,公示无异议后,便予以任命上岗。随着2017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228名入额检察官宣誓就职,全国检察机关已有8.7万多名员额检察官产生。
(二)退出状况。员额制改革取得成效后,为了保证检察官职业保障取得深入发展,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对检察官工资制度试点方案进行调整,基本形成了检察机关内部三类人员、两种待遇的格局,检察官待遇高于同级别公务员显而易见。仅从我省实际来看,员额制检察官工资套改去年11月已经完成,绩效奖金今年5月已开始兑现,工资待遇均有不同程度涨幅,但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工资改革尚未进行。这样在检察机关内部,员额制检察官的主体地位愈加凸显,利益调整的幅度更加明显,“入额”人员一下成为关注焦点和向往的目标。试想,已经享受到如此高的待遇,从人的本性来讲,主动退出勉为其难,劝其退出却依据不足。仅在笔者所在市,现在还未获悉到员额检察官退出情形,相反在司法行政岗位“入额”人员纷纷辞去行政职务的比比皆是。但从新闻媒体中看到,江苏、山西、安徽、贵州、上海等地已经出台了退出管理机制,江苏目前已有68名员额检察官因任职回避、离开司法办案岗位等原因退出员额。重庆市为防止司法办案中发生利益冲突,该市检察机关对配偶、子女为从事有偿服务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15名员额制检察官,实行了“单方退出”,不一枚举。从理论上员额检察官退出的步履维艰与现实工作中的逐步推行叠加而至,员额检察官退出现状参差不齐。
二、建立退出机制的必要性
(一)“有进有退”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哲学通说“进与退”是相对概念,无退则无所谓进,反之亦然。“进、退”具有辩证关系的并列行为,必须确立两者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强调一个方面。另外从汉语言角度来看,宋朝秦观《主术策》:“非有政事之臣,则百官之进退,奈何而不乱也”,其间“进退”就有升降、任免之意。员额检察官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终究是一种法律职务,必然有晋升、降职、任职、免职的规定,如2008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发布了《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员额检察官有遴选入额的具体规定,必然相对应建立退出机制,保证“有进有退”,遵从客观规律。
(二)有利于调动员额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在如今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大框架中,员额检察官既得利益有目共睹,也正是这一职业尊荣更能使其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已“入额”,我获得了高于同级公务员的待遇,一路走来,经过司法考试、遴选考试、逐级考核,着实来之不易。如何保持自我发展,不断晋升职务才是其主要的思考方向,至少不能退出员额,保持现存的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从这种维度考虑,多办案、办好案则是其工作的出发点。即就是从底线思维来讲,不做有违规定之事,否则退出员额,失去既得利益,何人愿为。
(三)有利于激发非员额工作人员的主动性。检察辅助人员是员额制检察官的后备军。特别是检察官助理,他们参与办案,除了对案件没有决定权外,其他诸如阅卷、讯问犯罪嫌疑人、起草文书等办案必经程序,他们都可全程参与。尤其是原来担任过检察官,只是由于受员额检察官比例的限制,在遴选考试或考核中失利,未能“入额”,他们的办案经验和历练值得肯定。一旦员额制检察官退出机制建立完善后,在退出缺额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加倍努力,竭尽全力从后备军转为正规军。
三、建立退出机制的主要内容
从目前各省份公布的员额检察官退出情形来看,江苏省规定:入额检察官一旦办案绩效达不到考核标准,连续2年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在司法办案工作中有重大过失、怠于履职等5种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出员额。山西省规定:员额制检察官退出员额的情形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被动退出,包括6种应当退出员额的情形:另一类是主动退出,即员额制检察官辞职的情形。安徽省规定:员额内检察官不能依法全面履职或履职不当造成不良后果,可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批评教育、离岗学习、扣发或不发绩效奖金、暂停履行职务、暂缓晋升检察官等级和退出员额等6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以上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出台相应退出情形,规定不相一致,笔者认为在建立退出机制中应包含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两种情形。
(一)主动退出:指已入额检察官根据自己实际状况或者依据相关规定已不能胜任工作,主动提出退出员额的情形。给员额检察官主动退出的权利,不仅尊重了他们的意愿,而且实现了人员的良性互动,促使员额制检察官管理充满活力。笔者认为主动退出应包含以下具体内容:一是经过一段时间员额检察官的工作后,自己认为不适合该工作岗位,不愿意从事员额检察官工作的;二是辞职、辞退、调动、退休等自然减员,已经离开员额检察官工作岗位的;三是本人入额后,配偶或者子女在本辖区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等工作,对方不愿退出现岗位,自己主动提出的。
对于上述自然减员情形,在其离开员额检察官岗位的同时主动提出的,自然按照退出程序做出决定。而一些员额检察官自己并不主动提出,政工部门应及时将此种情形纳入退出程序。
(二)被动退出:指根据员额检察官的工作表现,其已不能或不适合在员额检察官岗位继续工作,通过一定程序,对其做出退出决定的情形。员额检察官是一种职务,也是一种岗位,必然有具体的要求,一旦其在工作中出现某些问题,已不能或不适合在该岗位上工作,必须及时做出退出决定,让庸者下,能者上,保证人员良性循环。笔者认为被动退出包含以下主要内容:一是由于工作不认真,工作能力差,办案效率低,在绩效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 二是在司法办案工作中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办理错案,应当承担司法责任,不宜担任员额检察官的;三是因违纪违法行为受到相应处分,不宜担任员额检察官的;四是从事非检察业务工作的领导入额后,没有免去或没有依照承诺主动辞去其行政职务的;五是办案数量、质量达不到员额检察官基本要求,已不能胜任员额检察官工作;六是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在员额检察官岗位继续工作的。对于有被动退出的情形,如果员额检察官主动提出退出的,则按照相应程序进行处理,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并不是一成不变,只是一种化分而已。
目前中央政法委明确规定:政工部门负责人、纪检组长入额的,必须要辞去行政职务,否则必须退出员额。该规定仍有商榷之处,在实际工作中,政工部门负责人、纪检组长一般担任院党组成员,大都经过业务部门的历练,是一级一级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绩被组织提拔使用的。虽然从其职务定位来看,均从事非业务工作,但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政工部门负责人、纪检组长是检委会委员,依然从事业务工作,为此笔者将被动退出第四条退出情形的前提规定为:从事非检察业务工作的领导。唯有如此,才能符合客观实际,而不能一网打尽。
四、员额检察官退出的程序
目前,对员额检察官退出的有不同的规定,如江苏省:对员额检察官具有退出员额情形的,县(市、区)院党组研究提出意见,报设区市院审核后,报省院政治部审查。设区市院对本院员额检察官具有退出员额情形的,院党组提出意见报省院政治部审查,省院政治部提出审查意见,报省院党组审批决定。贵州省:依照程序退出员额,报省院政治部备案。安徽省:最终是否退出员额,需由省检察院决定。
从以上情况来看,员额退出有省级检察院党组决定和省级院政治部备案两种做法。笔者认为以上做法需探讨,员额检察官的遴选和退出应相辅相成,如今按照中央司法体制改革规定,每个省都建立了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遴选程序虽然首先要经过检察院内部运作,但是最终由省遴选委员会决定,省级检察院并没有遴选的最终决定权。进与退是事物的两个方面,给予省遴选委员会遴选决定权,不给于退出决定权,由省级检察院决定,一是违反了对事物决定权应统一的普遍规律。二是在实际工作中有可能出现这样情况:某位员额检察官因符合某种退出情形,被省级院做出退出决定,而后,退出情形消失后,其又经过遴选程序,被提交到省遴选委员会,而省遴选委员会已对其遴选过,会给遴选委员会造成重复遴选的错觉,显然对省遴选委员会的权威有所影响。这里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省遴选委员会只负责遴选,能否负责退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员额检察官的退出决定权交由省惩戒委员会负责较为妥当。一是省遴选委员会和省惩戒委员会均都建立,各省份法院检察院遴选、惩戒委员会的在人员组成和运作方式上不尽相同。例如,上海、陕西等省份采取“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做法,法官检察官遴选与惩戒委员会人员重合,吉林、海南等省则分设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和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人员组成有所不同。按照遴选与退出相对应的说法,由省惩戒委员会负责员额检察官退出事宜更为适合。二是在员额检察官退出情形中涉及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发生错案或受到处分情况,对此由省惩戒委员会做出否定评价,让其退出更为适宜。三是省遴选委员会、惩戒委员会大都是法院、检察院之外聘请人员组成,做出的决定更为客观,以防内部操作有包庇之嫌。在省惩戒委员会做出退出决定后,及时向省遴选委员会进行通报,保证二者无缝衔接,就不会出现笔者上述出现重复遴选的错觉,如遴选与惩戒委员会是“一套班子”,自行备案即可。
在检察机关内部操作层面,应有政工部门受理,院绩效考核委员会决定,再层级上报到省惩戒委员会做出最终决定。目前普遍采取由院党组决定的做法值得商榷。绩效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不仅包括院领导、一些部门领导,而且会吸纳优秀的检察官,人员组成较为广泛,对员额检察官工作情况了解较为全面和真实。院党组虽有人员的任免权,但其人员组成没有绩效考核委员会多,再者对退出情形中工作不认真、能力不强、办案效果差,绩效考核两年在基本称职以下的认定,由绩效考核委员会认定更能服众。对于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两种情形,只是程序启动的源头不同,主动退出由员额检察官自行提出或者出现自然减员的,附相关文件,被动退出由发现者提出,政工部门受理,再统一由院绩效考核委员会做出是否退出的意见,决定退出的向上级层报,由省级惩戒委员会做出最终决定;决定不退出的继续留任,但需向上级备案,上级认为应当退出的,撤销不退出决定,最终由省惩戒委员会决定是否退出,真正使员额检察官退出程序严格和务实,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山西晚报2017年2月16日 我省建立员额制检察官退出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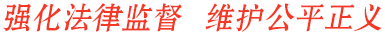
 头条
头条 微博
微博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